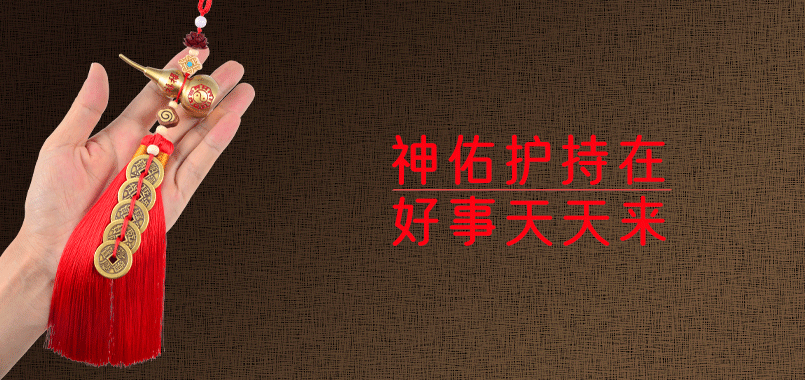朱仙镇木版年画:年俗里的活化石,刻版师傅手把手教你雕出‘门神’的精气神

腊月的朱仙镇老街飘着两股味道——前半段是炸麻花的甜香,后半段突然就被松烟墨的醇厚和梨木的清苦截住了。顺着味儿拐进“张记年画坊”,73岁的张铁山师傅正伏在案子上,刻刀在半块梨木板上走得细碎,木屑像金色的雪片落进竹筐。
“您这刻的是秦琼还是尉迟恭?”我凑过去问。老人没抬头,刻刀在“武将”眉骨处轻轻一挑:“秦琼。你看这眼角,得往下耷拉半分,威严里带点慈,像家里最能镇场子的老叔。”他推了推老花镜,指节上的老茧泛着琥珀色,“去年有个北京来的姑娘,刻门神时把眼睛雕得太凶,我说这不成,门神是守家的,不是吓人的。”
朱仙镇的木版年画,确实是守家的老物件。北宋时这里是汴京的南大门,年画铺子沿着运粮河排开,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说“十二月近岁,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”,说的就是这门手艺。张师傅的爷爷曾在大相国寺旁开坊,他从小看惯了——冬闲时,男人们在院里晒版,女人们坐在门槛上刷色,孩子们追着飘落的“加官进爵”纸片跑。“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请门神,不是图花哨,是图个踏实。”
刻版是门慢功夫。张师傅的案子上摆着十多把刻刀,大的像小铲子,小的细如缝衣针。“先选料,得是三年以上的黄梨木,晒足一百天,没裂缝才能用。”他抽出一块半成品,正面是用墨线勾好的门神轮廓,“画稿要反着描,刻的时候得跟着反稿走,等印出来才是正的。”说着他操起“平口刀”,沿着墨线轻轻推,木屑卷成小卷儿飞起来,“这刀要使巧劲,推深了版会裂,推浅了印不清晰。”
最见功夫的是“开脸”。张师傅放下刻刀,用拇指抹了抹“秦琼”的额头:“眉眼是门神的魂。你看这双眼睛,得雕出‘眼尾挑、眼仁沉’的劲儿——挑是镇得住邪祟,沉是容得下烟火。”他说起去年带的学徒小周,这孩子在深圳做UI设计,过年回家看见爷爷贴的年画褪了色,当场辞了职。“小周第一回刻眼仁,刻废了三块版,急得直拍桌子。我跟他说,别急,你听这刻刀响——‘咔嗒咔嗒’,像不像老辈人在跟你说话?”
说话间,木版上的秦琼渐渐有了生气:甲胄的鳞片根根分明,手中的双锏泛着冷光,最妙的是那对眼睛,白天看威严,夜里借着月光瞧,竟像含着点笑。“前儿有个妈妈带孩子来体验,小姑娘刻坏了半块版,急得要哭。我捡了块木屑给她,说你闻闻,这是木头的香,也是年的味道。”张师傅把刻好的木版往印台上一放,刷上松烟墨,覆一张生宣,用棕刷轻轻一擦——红袍金盔的门神“呼”地跳上纸来,连鬓络腮胡都根根分明。
“现在年轻人都说‘仪式感’,可真正的仪式感,不就是这些磨手的刻刀、染黑的手指、落了灰的老版子吗?”张师傅望着窗外飘起的雪,老街的灯笼已经挂起来了,“我这儿存着百来块老版,最老的是光绪年间的‘加官进爵’。有时候半夜起来看版,就觉得这些木头片子会说话——它们在说,日子要往下过,老理儿不能丢。”
你见过刚印好的门神吗?墨香还没散,颜色鲜得像要滴下来,贴在门上,风一吹,那甲胄上的金线好像会动。这哪是张画?这是刻在木头上的年俗,是老一辈传给我们的“安心符”。下次过年,不妨去朱仙镇走走,握握那把刻刀,听听木屑落下的声音——你会明白,有些东西,刻进木头里,就刻进了血脉里。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31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