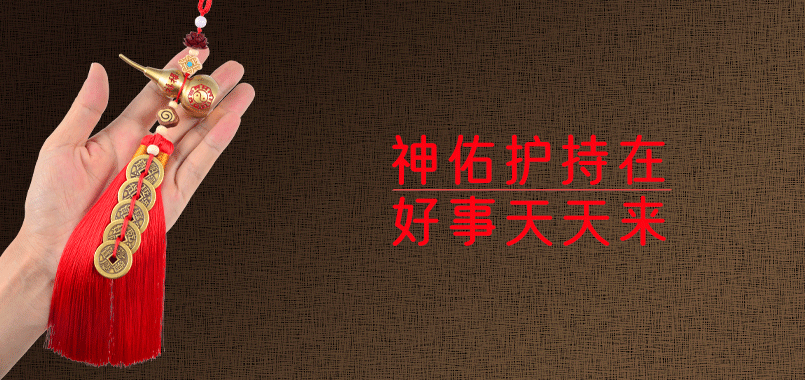钧瓷:入窑一色出窑万彩,揭秘禹州匠人的‘窑变魔法’与千年瓷魂

在禹州神垕镇的老街巷里,青砖灰瓦间总飘着若有若无的陶土香。我蹲在王松茂师傅的作坊前,看他用粗粝的手指抚过未上釉的素坯——那些被称作"泥娃娃"的瓷胎,此刻还只是普普通通的土黄色,谁能想到,几天后从1300℃的窑炉里出来,它们会变成被晚霞吻过的"海棠红"、浸着月光的"天青",甚至是流动着银河的"星辰紫"?
"这就是钧瓷的脾气。"王师傅笑着往釉缸里蘸取青灰色釉浆,手腕轻旋,釉水便像春雪化溪般漫过坯体,"入窑时都是素色,可窑火一舔,釉里的铜、铁、钴就活了,在胎骨上跳舞、打架、融合,最后变出谁都猜不透的颜色。"他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釉料渍,这是守窑三十载的勋章。
记得去年深秋,我曾见证一窑开炉。窑门刚打开,热浪裹着松烟味扑出来,王师傅的徒弟阿林举着长钳的手微微发抖——这是他独立烧的第一窑。当那只荷叶盏被夹出来时,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:盏心是浓郁的茄皮紫,边缘却晕染着一圈粉金,像极了雨过天晴后,天边那道不肯散去的霞。"成了!"王师傅突然喊出声,我看见他眼角泛着水光,"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开窑,烧出个蚯蚓走泥纹的笔洗,我师父也是这样掉眼泪的。"
这眼泪里藏着钧瓷的命。北宋徽宗年间,钧窑被钦点为"御用珍品","纵有家财万贯,不如钧瓷一片"的说法流传开来;可到了清末,战火与饥荒让钧窑断烧近百年,最后一任窑主把配釉秘方缝进棉袄里,在逃难路上冻成了冰雕。直到上世纪50年代,几位老匠人翻遍古籍、试了上百次釉方,才让钧瓷的火焰重新烧起来。王师傅的师父就是其中一员,他常说:"钧瓷不是死的,它是活在火里的魂。"
如今的神垕镇,窑炉的数量比二十年前多了十倍,可真正能烧出"窑变绝品"的,还是那些守着柴窑的老匠人。有人劝王师傅换电窑,温度能精准到1℃,省得熬夜看火。他却蹲在窑前拨弄松枝,火星子溅在脸上:"电窑是准,可松柴燃烧时的挥发物会钻进釉里,那是机器造不出来的灵气。你闻闻,这松烟里带着山岚的味道,钧瓷要是没了这股子烟火气,和超市里的碗有啥区别?"
更让人安心的是那些"接棒"的年轻人。阿林大学学的是工业设计,却放弃了深圳的高薪,回来跟着师父搓泥拉坯。他在传统釉料里加了点现代矿物,烧出的"星空盏"在国际工艺展上拿了奖。"有人说我改了老规矩,"他捏着半干的坯体,指腹压出一道浅痕,"可您看这蚯蚓走泥纹,不也是窑温不均时自然形成的'缺陷'?老祖宗都能把缺陷变成美,我们为啥不能让钧瓷多几副新模样?"
暮色里,又一窑要封门了。王师傅往窑口抹最后一把泥,火舌从观火孔里窜出来,把他的脸映得通红。我突然明白,所谓"千年瓷魂",从来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老物件,而是这些守着窑炉的人——他们把青春揉进泥里,把岁月烧进釉里,把对土地的眷恋、对美的执着,都交给那一窑又一窑的未知。
下次你来神垕,不妨蹲在窑前等一场开炉。当那层蒙着灰的釉面在你眼前慢慢显露出颜色时,你会听见千年的风穿过窑门,带来最古老也最鲜活的答案:有些美好,注定要在不确定里生长;有些传承,从来都藏在匠人的骨血里。就像王师傅说的:"窑变没有魔法,有的只是——我信这土,这火,信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,更信,总有人愿意接着守下去。"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30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