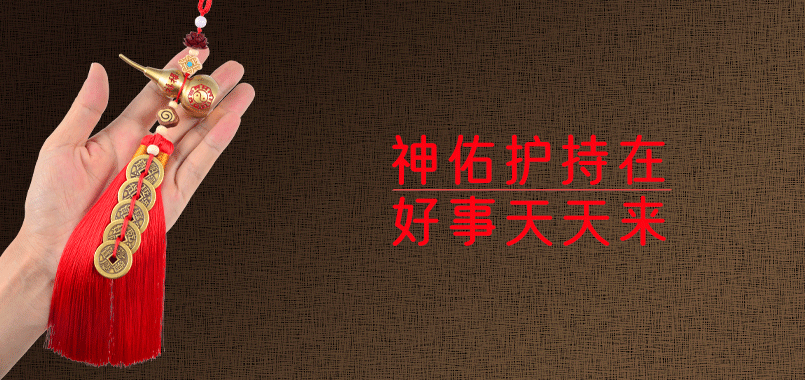佛山木版年画:雕版印出的年俗记忆,看老匠人的手工秘籍

推开祖庙旁那扇有些年头的木门,混合着墨香与木屑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七十岁的冯兆强师傅正俯身在工作台前,刻刀在梨木板上轻轻游走,刀背敲打的“笃笃”声里,一张红脸关公的眉眼正从刻板里慢慢“醒”过来。
“你看这线条,得顺着木纹走。”他抬起头,老花镜滑到鼻尖,指节粗大的右手还沾着深褐色的墨渍,“我爷爷光绪年间就在祖庙摆摊印年画,那时候整条街都是‘刷’‘刷’的拓印声,小孩蹲在边上捡裁剩的红纸片,比现在过年放鞭炮还热闹。”
佛山木版年画的根,扎在宋元,旺在明清。我曾在博物馆见过清乾隆年间的“秦琼敬德”门神,朱红底上金粉勾勒的甲胄,历经两百年依然鲜亮。冯师傅说,过去家家户户贴年画不是为装饰,是“请神仙”——大门贴门神镇宅,灶头贴灶君司火,床头贴“子孙昌盛”讨彩头。“那时候穷人家买不起新画,就把旧年画揭下来补补再贴,说‘老神仙认门,换了地方要迷路’。”他笑起来,眼角的皱纹里浮着点湿润。
最让我入神的是雕版环节。冯师傅的刻刀有七八种,薄如柳叶的修线刀,半圆口的铲底刀,还有专门挑毛刺的尖锥。“刻反字最考验功夫,”他递过一块刚刻好的“福”字版,“你看这横,左边要深半分,拓印时才不会糊;右边收锋得利落,不然福字要‘塌肩膀’。”阳光透过木窗斜照在刻板上,梨木的纹路像流动的琥珀,那些反刻的线条在光影里明明灭灭,竟有种对称的美感。
有次看他教徒弟阿林刻“花开富贵”,阿林连刻坏三块版,急得直搓手。冯师傅没说话,把自己用了三十年的刻刀递过去:“这刀跟了我从学徒到师傅,刀把磨得发亮的地方,是我爹当年手把手教我时握的位置。”阿林接过刀,突然红了眼眶。后来阿林告诉我,那天他刻到深夜,听见冯师傅在门外轻声说:“慢点儿没关系,刻坏的版都是学费。咱们这手艺,最怕的不是刻坏,是没人接着刻。”
现在每到腊月,冯师傅的工作室就变成小庙会。有老人带着孙辈来挑“金童玉女”,说要贴在祖屋正堂;有年轻人举着手机拍拓印过程,发朋友圈配文“这才是中国年的底色”;还有外国游客蹲在边上,看红纸上渐渐显露出的牡丹、蝙蝠,嘴里直念叨“magic”(魔法)。冯师傅拓印时总留半张纸的空白,“给人写个‘福’字,或者画朵小花,这年画就成了自家的。”他指着墙上一张褪色的老照片——年轻时的他站在年画摊前,身后是整面墙的“花开富贵”,“那时候觉得这手艺再普通不过,现在才明白,咱们印的不只是画,是年的味道,是一代又一代人记得回家的路标。”
暮色渐浓时,冯师傅用软毛刷轻轻扫去刻板上的木屑,把最后一张“门神”小心卷进牛皮纸筒。窗外传来隔壁茶铺的粤剧唱腔,“一入腊月门,烟火照归人”——我忽然懂了,为什么这褪色的雕版能刻出最鲜活的年俗记忆。因为每一刀下去,都是老匠人在跟岁月说:“你看,我还在,这手艺还在,年的味道,永远都在。”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288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