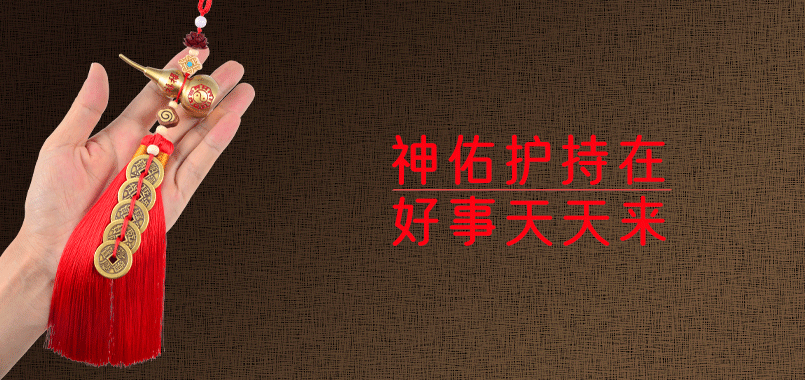石湾陶塑:泥火交融的岭南雅韵,揭秘非遗陶匠的捏塑绝技

晨雾还未散尽时,石湾镇的陶坊已飘起湿润的土腥气。72岁的梁伯蹲在工作台前,指尖沾了水,正对着半成型的"渔翁"陶坯轻轻摩挲——他的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陶泥,像岁月刻下的暗纹。这是我第三次来拜访这位省级非遗传承人,每次推开那扇红漆斑驳的木门,总觉得时间在这里走得很慢,慢得能听见陶土呼吸的声音。
"你看这泥,得挑北江冲积的河泥。"梁伯捏起一团深褐色陶泥,在掌心揉出油润的光泽,"要反复摔打七七四十九遍,把空气都赶出去,捏出来的胎骨才结实。"他的手像会变魔术,刚才还软塌塌的泥团,经他拇指一压、食指一推,转眼间就隆起渔翁微驼的脊背。我凑近些,看见他指腹的老茧在陶坯上压出细密的纹路,"这叫'压塑法',力道得像哄睡孩子——太轻留不下痕,太重又会塌。"
石湾陶塑的历史,要从宋代说起。从前的石湾人靠烧窑为生,"石湾瓦,甲天下"的说法传了几百年。可真正让我震撼的,不是那些摆在博物馆里的精美摆件,而是梁伯说的"活态传承"。去年冬天,他带着徒弟在陶坊里做"关公",为了还原武将的霸气,特意去武馆看了三个月的刀术。"刀穗要飘得有劲道,衣纹得跟着力道走。"他指着案头未完成的陶像,"你瞧这衣摆的褶皱,得用竹片挑出层次感,像风吹动的旗子,可又不能太飘——关公是武神,得稳。"
最让我难忘的是开窑那天。陶窑的火舌舔了三天三夜,终于到了开窑时刻。梁伯戴着厚手套,慢慢掀开窑门,热气裹着松木香扑出来。当那尊"渔翁"出现在眼前时,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:深褐色的陶胎泛着温润的光,渔翁的斗笠边缘挂着釉滴,像刚从雨里走出来;他腰间的鱼篓歪着,里面躺着三条半露的鱼,一条尾巴还翘着,仿佛下一秒就要蹦出来。"成了!"梁伯突然笑出声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,"这窑的火候拿捏得刚好,釉色渗进泥里,像茶渍浸了老棉袍,有年头的味道。"
可传承哪有这么容易?梁伯的徒弟里,有两个年轻人去年转了行。"现在的孩子坐不住啊,捏个泥人要练三年基本功。"他蹲在陶泥堆前,声音突然轻了,"有回我教小周捏'钟馗'的胡须,他说用机器刻更快。我跟他说,机器刻的是死的,人捏的是活的——你看这根胡须,我多搓半下,就有了风的方向。"说罢他拈起竹刀,在陶坯上划出几缕细丝,真像有清风正从钟馗的耳边吹过。
暮色漫进陶坊时,梁伯把最后一抔陶泥收进木匣。窗外的榕树沙沙响,他望着满墙的陶像,突然说:"你知道吗?每块陶泥都是有脾气的。有的泥软,适合做飘逸的仙女;有的泥硬,得用来塑威严的菩萨。我捏了五十年,现在闭着眼都能摸出泥的性格。"他的手抚过"渔翁"的脸庞,像在摸自己孩子的头,"等哪天我捏不动了,只希望有人能接着跟这些泥说话——它们等了千百年,就为了在人手里活过来。"
离开陶坊时,晚霞把屋檐染成了琥珀色。我回头看,梁伯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和那些未完成的陶像叠在一起。突然明白所谓"非遗",从来不是玻璃柜里的标本,而是一双手传给另一双手的温度,是泥与火的对话里,永远跳动着的、鲜活的心跳。下次再来,不知道梁伯又会捏出怎样的故事?或许是个挎着竹篮的村姑,或许是头摇着尾巴的老黄狗——但我知道,每一件作品里,都藏着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注脚。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290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