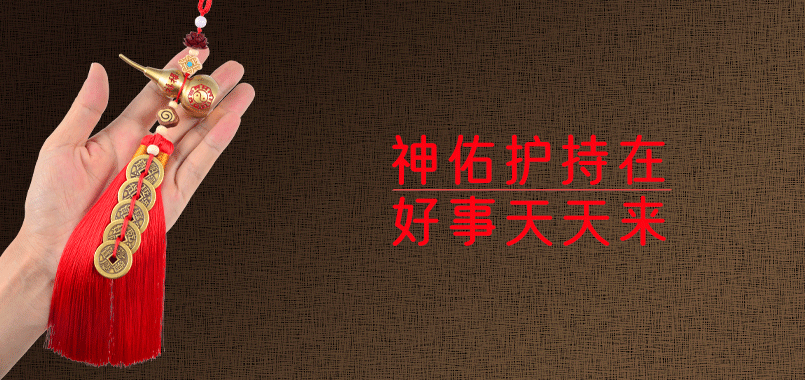潮州木雕:木作里的立体诗画,看匠人如何刻出千年潮韵

清晨的老作坊总带着股独特的香气——是新剖的樟木混着陈年木屑的清甜,混着红漆的暖,混着老木头被岁月浸出的沉。我站在门槛外,看李阿公的刻刀在一块木料上游走,刀锋起处,木屑像碎雪般簌簌落进竹篮。他今年七十有二,背已微驼,可握凿子的手稳得像山,指节上的老茧泛着琥珀色的光,那是六十年刻刀磨出来的年轮。
"你看这牡丹,花瓣要分七层。"他忽然抬头,老花镜滑到鼻尖,"最外层是舒展的,用圆雕;中间层得留些镂空,透雕才能见光影;最里层的骨朵,得用线雕慢慢挑——跟画工笔似的,急不得。"我凑近些,看见他刀下的木面正慢慢长出花形:最外一片花瓣边缘带着毛茬,那是刻意留的"刀味",像真花被风掀起的褶皱;往里一层却光滑如缎,刀锋走得极慢,能看见木头的肌理顺着花瓣走向流淌。
潮州木雕的岁数比李阿公大得多。我曾在开元寺见过一尊北宋的木佛龛,虽历经千年,莲花座上的卷草纹仍清晰得能数清叶脉。当地人说,明清时更盛,大屋的梁架、神龛、屏风,甚至床楣、妆奁,但凡能雕花的地方,都要刻上"郭子仪拜寿""百鸟朝凤"——那是过日子的讲究,也是刻在木头里的故事。己略黄公祠的金漆木雕最是有名,我去看过,门楣上的"铜雀台"场景里,连侍女发间的珠钗都刻得根根分明,阳光斜照时,那些镂空的窗棂影子落在地上,像幅会动的古画。
"以前讲究'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'。"李阿公放下刻刀,用软毛刷扫去碎屑,"你看这对狮子滚绣球,绣球里藏着石榴,石榴籽是多子;狮子脚下踩着卷草,卷草不断头,是长寿。"他指尖抚过木料,像在摸自家孙儿的脸,"现在年轻人爱刻些新花样,上个月有个姑娘来学,说要刻潮绣的纹样,还要加进广济桥的元素——倒也有趣,老木头能装新故事,才活得长。"
我问他最苦的时候是什么。他想了想,眯起眼笑:"八十年代那会,没人要木雕了,我去做家具,刻些简单的花纹。有回给人打床,人家说'别刻花,费钱',我握着刻刀站在木料前,突然觉得这手生分了。"他摊开手,掌心里有道旧疤,"后来儿子说要去深圳打工,我没拦。有天他打电话回来说:'爸,我在博物馆看见你刻的神龛了,解说员说这是国家级非遗。'我蹲在院子里哭了一场——原来我们刻的不只是木头,是人家记着的东西。"
去年秋天,李阿公收了三个徒弟,最小的才二十岁。我去作坊时,正撞见他们围着块木料争论:"这只凤凰的尾羽该用深浮雕还是透雕?""透雕更灵动,但木料薄了容易断。"李阿公坐在竹椅上打毛线,偶尔插句嘴:"你们试试先画样,拿薄纸拓在木头上,用针戳出点,再下刀——我师父教我的法子。"阳光透过木窗,在他们脸上投下细碎的影,那些年轻的手指捏着刻刀,像在握一团跳动的火。
现在走在潮州的老街,常能撞见木雕的影子。民宿的隔断用镂空的梅兰竹菊,茶空间的挂屏刻着韩江的山水,连咖啡店的菜单牌都是樟木刻的,边缘故意留着毛边,像从老房子拆下来的旧料。有回在牌坊街,看见个穿汉服的姑娘举着手机拍门额的木雕,对着同伴喊:"你看这只蝙蝠,刻得多生动!'蝠'就是'福',古人多会讨彩头!"
李阿公说,木头是有魂的。好的木雕,远看是幅画,近看是首诗,摸上去——他拍拍案头的木料——是温的,像有人刚摸过。那些被刻刀唤醒的纹路里,藏着唐宋的风,明清的月,藏着阿公师父的叮嘱,藏着小徒弟们的窃笑,藏着所有把日子过成诗的人,刻在木头上的,最鲜活的潮韵。
暮色渐浓时,李阿公又埋下头。我听见刻刀与木头的轻响,一下,两下,像心跳,像呼吸。忽然懂了他说的"木头有魂"——那魂,是手艺人的温度,是文化的血脉,是所有被认真对待过的时光,在木头上,刻成了永不褪色的诗。
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。https://i199.art/chuangyishougong/2295.html